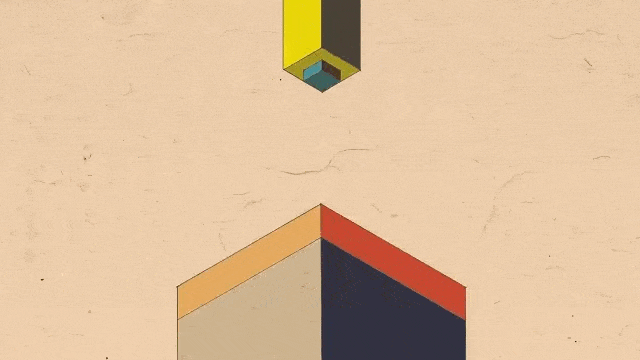“抽象并非涂抹空洞的几何,也不是背离自然——它是去除自然里那些束缚的外壳,使我们触及看不见的核心秩序。”
——改写自蒙德里安书信
一、在理性与神秘之间:蒙德里安的生平与早期探索
蒙德里安
1872年,蒙德里安(Piet Mondrian)出生在荷兰的一个教师家庭。他从小接受相对严谨的教育,父亲是绘画老师,在家乡小城冥想之余,也常到乡间素描。青少年时期,他画的风景题材多带印象派余韵,色彩明丽且笔触灵动。
《草垛》
但在1908年前后,他逐渐与神智学(Theosophy)思想相遇,这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哲学流派,强调对“世界本质”的冥想与对“精神层面”的探索。由此,蒙德里安对于“自然”开始抱有一股截然不同的热情:
不再满足于对外表的再现,而想探究万物内部是否暗藏某种“数学”或“和谐”
这一时期的“树”,就是他艺术转折的象征:
最初的《红树》(约1908)与《灰树》(约1912),保留了具体枝干与略带象征主义的色彩。
《红树》
《灰树》
随后,蒙德里安对树的结构进行了愈发激进的抽离,让枝桠转化为交错的线与块面——《花开之树》《构成中的树干》等画作中,已能看出他有意将自然的繁复拆解为某种内在“纹理”。
《花开之树》
进入1914-1915年,他的线条发展到几乎看不出树形,只剩纵横交错的黑色与灰色区隔,好像为后来的“纯抽象”埋下伏笔。
Composition of Trees, 2
二、走向极简格子:从“新造型主义”到几何绝对化
1917年,蒙德里安与范杜斯堡(Theo van Doesburg)等人共同创办了著名的《风格》(De Stijl)杂志,这标志着“新造型主义”(Neo-Plasticism)的正式成形。其核心主张是:
“舍弃一切具象与装饰,使用最基本的垂直与水平线,以及原色(红、黄、蓝)与中性色(黑、白、灰)。从而在画面中呈现一种理性的、普遍的秩序。”
《百老汇爵士乐》
在这一阶段,蒙德里安的作品开始出现我们最熟悉的网格结构:《红黄蓝的构成》《百老汇爵士乐》等等。那些横竖的黑色线条将画面分割成矩形或方块,填上原色或干脆留白。这不再是“风景”或“树干”的画作,而是对“视觉基本单位”的大胆信仰。
《红黄蓝的构成》
他认为,纵横线代表自然与人文、阳性与阴性、动与静等对立的融合。
色彩的极端简化意在消除“个人情绪”,达到某种带有哲学意味的“普遍和谐”。
这一过程,若追溯到最早那棵“树”,我们能感觉到他的主观野心:要将“有机且混沌”的万事万物,硬生生提炼成抽象骨架。这种骨架,虽近乎冷酷,却在蒙德里安眼里恰恰是一种“永恒的几何秩序”。
Composition Noll
三、抽象动画的暗流:从费辛格到日本实验动画
蒙德里安并未直接涉足动画,但他的理念却对20世纪的抽象动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。动画,尤其是实验动画,往往追求的不是叙事和角色,而是视觉与时间的交响。
1. 费辛格(Oskar Fischinger, 1900—1967):几何律动
在欧洲,奥斯卡·费辛格可谓最早把“几何抽象”变为“动态艺术”的先驱之一。他创作了许多短片,通过色块、线条的旋转与消长,配合音乐节奏,营造一种颇具蒙德里安式的“绝对构成感”。如果说蒙德里安的格子画是静态的几何分割,那么费辛格就让它“站起来”舞蹈。在他的作品《Motion Painting No.1》中,你可以看到类似“水平、垂直与色彩形状”在流动中渐变、组合、瓦解——几乎就是用胶片再现“几何变奏曲”。
《Motion Painting No.1》,截图
2. 日本:当几何遇上新媒介
日本动画工业在世界闻名,但绝大多数作品还是以叙事、角色为依托。然而,若深入到小众独立动画领域,就能看见对蒙德里安式抽象理念的呼应。
水江未来(Mirai Mizue)常用密集的几何形或“细胞形”不断分裂、组合;他甚至曾做过每天绘制一秒的短片项目(《MODERN No.2》系列),以纯粹的形与色展现连续变化。那种持续的视觉节奏,几乎与蒙德里安的“格子”思路一致:将繁复世界精简为最“原初”的单位。
其他日本实验动画导演,也常在国际动画节上呈现类似的无角色、无故事作品,这些短片以“几何互动”或“色彩律动”为核心,用抽象形式直击感官。
《MODERN No.2》
虽然并不能说他们直接承袭了蒙德里安,但“去叙事、只存形与色”的思路,与蒙德里安“去自然表象、只存绝对秩序”的做法无形中相互呼应。
四、“网格”的现实——蒙德里安对当代动画意味着什么?
蒙德里安对“最小可视单位”的执着,启发了许多动画人的创作思路:在一帧帧的画面中,如果我们把“具象角色”抛开,就能使用“点、线、面”本身来设计出节奏。他的红黄蓝与水平垂直线,本质上是对图形语言的极限实验——动画师若想突破传统角色的束缚,也常会用类似的极简几何与色彩区隔,来取得一种强烈的张力。
凉宫春日的忧郁06版OP
蒙德里安的网格有时被批评过于理性、冷酷,也有人称其为“扼杀自然之美”。在动画领域,走抽象路线也面临类似风险:观众可能感到难以共情,甚至会质疑这类作品有无商业价值。然而,正是这份疏离与极简才形成了特有的锋芒——一种对庞大叙事体系的“主动逃逸”,直接冲击观看体验。这与一些实验动画作品强调“纯粹视听”是同一道理。
当我们回头看蒙德里安画那棵树,或许意识到:他其实在给后世动画人(乃至视觉艺术家)树立一个问题——你是否一定要用写实或人物描绘,才能表达世界? 通过对“树”的解构,蒙德里安用锋利的几何刀刃逼问艺术本质:当万物皆被解析成横与竖、红与蓝时,还有什么依附?动画人若在作品里做同样的拆解——去除角色、去除故事,又是否能创造新的世界逻辑?
菱形构图与双线,蒙德里安,日期不详
五、结语:那棵被切开的“树”,在动态中延伸
蒙德里安的生平与风格转变,可以简单归纳为:
1880-1900年代:受到父亲和学院派训练的影响,主攻风景与人物画。
1908-1912年:印象派与象征主义色彩的过渡期,“树”题材出现;同时接触神智学,转向对“内在秩序”的探索。
1914-1917年:战时回到荷兰,逐渐简化画面,树干只剩支离的线条。
1917-1920年代:参与“新造型主义”运动,正式确立垂直/水平+原色几何抽象的风格,并在巴黎与同辈艺术家互动。
1930-1944年:旅居巴黎、伦敦、纽约,以《百老汇爵士乐》等作品再度突破,最终形成标志性的网格体系。
这条从“自然树干”走到“理性网格”的路,很像一个持续剥离的过程:去掉多余的色彩,抹掉弯曲的轮廓,直到只剩最赤裸的直线与平面。于他而言,这既是一种艺术语言的开创,也是一场精神冒险——用极简对抗混沌。
而在动画的世界里,这种极简何尝不是另一种“冒险”?
欧美的费辛格把它玩成了几何交响乐,日本实验动画则将其融入生物般的形变与节奏。纵使表面形式迥异,其“抽象”的初心却都能追溯到蒙德里安那把锋利的几何刻刀。就像他拆解“树”那样,他们在“具象角色”“线性剧情”中找到了值得剥离的壳,指向更纯粹的感官秩序。
也许,我们可以想象一棵“动态的抽象之树”仍在生长:它的枝干不断分化成网格、分化成方块,透过胶片的闪烁或电脑的像素,继续延伸。蒙德里安并不曾在动画里亲自落笔,但他的理想,已在一帧帧光影中悄悄泛起回声——那棵早被他“切开”的树,终究还是在另一重维度里留下了自己的痕迹。
《自画像》,日期不详
写于2024/12/30,凌晨2:27。
来自:Bangumi